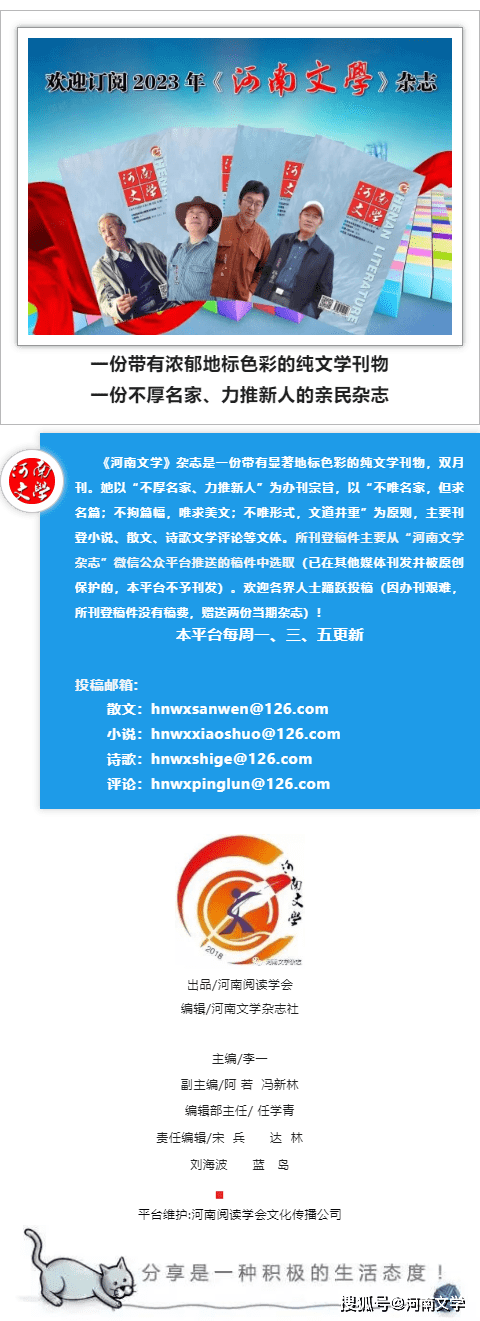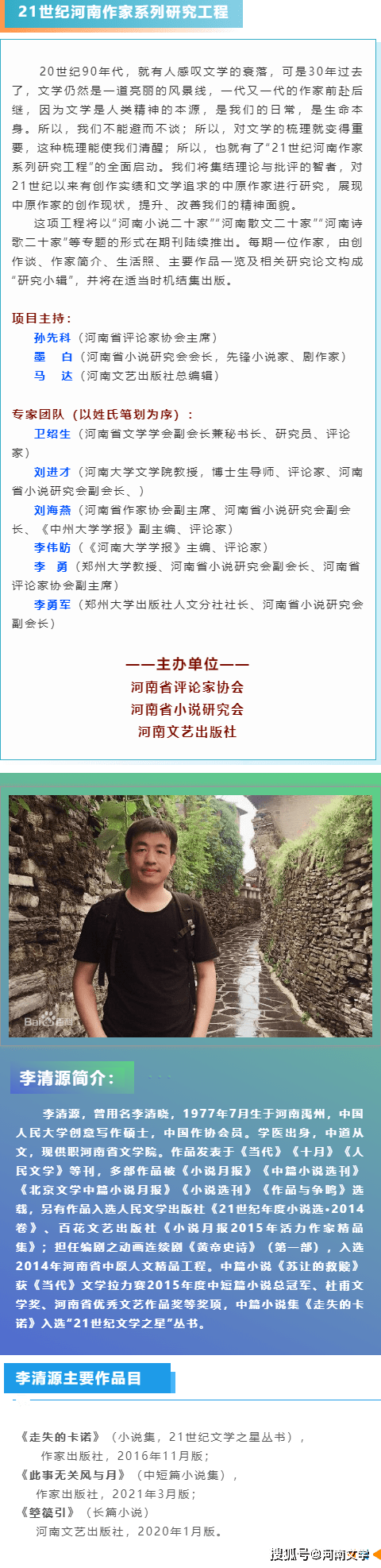

社会转型时代是一个风云激荡、泥沙俱下的时代,但却并非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不管我们用怎样一种浪漫的情怀和语言去想象它、描述它,我们都无法否认伤痛与困厄的存在。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身陷伤痛和困厄,然而那些身陷伤痛和困厄中的人们却是时代“伟业”的致命隐痛,犹如巨灵的“阿喀琉斯之踵”。面对这些,文学能做什么?文学并不承担必要的道德义务,但它却自有揭出这种隐痛的冲动。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近二十余年的文学基本都处于这样一种冲动之中,从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到新世纪的“底层写作”、“非虚构”文学,它们所关注的社会转型带来的问题、边缘人群(工人、农民)的生存处境,以及它们关注这些“问题”和人群处境的方式(现实主义写实)等,无不显现着文学的道德焦虑。
这种焦虑表现在描写对象的趋同——社会转型下的伤害与创痛;表现手段的一致——现实主义的写实;情感内质的相似——感伤、同情、悲悯、激愤。所导致的结果,最明显的即作品和表现对象之间无比切近的距离,这种距离有时达到了难分难解、近于消失的程度(如“非虚构”)。这种道德激愤下的写作,混合了各种各样并不纯洁的动机和目的(如商业化包装、成名的渴望),从而显得问题重重。文学的品质和个性难免受到损害。无论是“现实主义冲击波”,还是“底层写作”、“非虚构”文学,它们几乎一致地都受到过这方面的批评。而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像“底层文学”那样的直接关注社会转型的写作与新世纪初相比,似有落潮——至少已经退去了新世纪初的那种蜂拥而起的鼓噪和喧嚣,进入了一种似乎比较平稳缓和的发展态势。在这种态势下,社会转型叙事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存在哪些问题?我们不妨借河南青年小说家李清源的《苏让的救赎》进行分析。

《苏让的救赎》发表于《当代》杂志2015年第1期;《小说月报》2015年第2期予以转载;2016年获得河南省最高的文学奖——杜甫文学奖。这篇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它描写了主人公苏让救父的故事:出身农村的大学毕业生苏让,在省城过着漂泊无定的租房生活,在被靓丽出众的大学女朋友抛弃后,他又结识了身材一流、面貌倒数一流的新女友谢春丽,因为谢春丽貌丑而占据心理优势的苏让,时常有恃无恐地伤害女友,并终于有一天导致她离家出走,而这时恰恰又传来父亲打人被捕的消息,无暇处理感情危机的他连忙回老家营救父亲,然而费尽周折毫无效果,无可奈何的他试图卖肾救父,甚至想自杀……但就在山穷水尽之际,女朋友谢春丽终于暗伸援手,给他汇款、请律师,并打赢了官司,感激涕零的苏让返回省城后,经过一番努力也求得了一开始避而不见的女友的谅解,同时也把父亲苏克修接到了城里。
一个不甚复杂的故事,李清源的叙述却布设了玄机——首先是围绕苏让父亲被囚禁、苏让回乡搭救,建成主要的故事框架,形成叙事的主线;其次是围绕苏让和女朋友的关系,形成第二条辅线。二线并行。第一条线索下的故事,主要围绕苏让的父亲苏克修犯案被拘展开。苏克修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却因殴打女友而被警察拘捕。那么他女朋友是谁?为什么遭到她举报?真相是否像大家说的那样?这一系列疑问,造成了包袱和悬念,作者以苏让为视点对此一一解开。第二条线索下的故事是附着在第一条线索之上展开的,苏让的情感故事在作品开头也只是开了一个头,以苏让女朋友谢春丽的负气出走留下悬念,并在苏让回乡救父的过程中,通过苏让一步一步陷入绝境而一次次想起女友的好处却又一次次联系未果、寻之不见,让悬念步步增强。这样使得整个小说是在一种“悬疑”的气氛下展开故事和人物,从而吊人胃口,引人观读。
讲好一个故事是一个小说家基本的素质。李清源在这里显现了他的才华:他设置悬念、留下铺垫,并循序渐进、步步解疑,同时又强化细节(如谢春丽的丑)、制造冲突,从而成就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尤为难得的是,他的语言富有古意,一些文言句式、语法、用词,都显现了当代小说家(尤其是青年小说家)并不多见的古典文学修养。而且这种文言化、化文言的语言,也一定程度上使得小说的叙事干练、利落,从而也增加着它的可读性。
这部小说从题材来看,属于比较典型的社会转型叙事。它叙述的是一个关于底层的故事。但是,这里的“底层”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下岗工人等,而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苏让。当然,在小说中,苏让的父亲苏克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且他在小说中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但是与苏让相比,苏克修无论从在整个故事中的重要性,还是从在作者的“叙述”中所占的比重来看,都要稍次。作品围绕苏让救父,着力所呈现的是一个当代大学毕业生的生存困境。
这种生存困境首先表现在他的就业方面。通过小说我们知道,苏让大学毕业后,先是 “在一家养老集团谋了个职位”,但是薪资有限只能在省城租房度日;后来女朋友劈腿,他辞职离开——
辞职离开后,工作换来换去,竟没有一个如意的。他当过内刊编辑,应聘过民校教师,在几家半死不活的文化公司干过策划,还尝试过推销保健内裤和万能钙片,就差没进传销组织碰运气。在职场拼搏之余,他还坚持文学创作,写了大量诗歌散文和小说。如是奋斗了六年,他可悲地发现,愿望中的成功非但没有随着脱发速度的增加而日愈靠近,反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渐行渐远。文学作品攒起来亦几可等身,但是一篇也没在正经刊物上发表过。二十六岁那年,他看到一篇关于网络作家富豪的报道,怦然心动,于是辞掉工作,投身于网络写作。他从春天写到秋天,花光了所有积蓄,最后欠着一个月房租,灰溜溜地逃回了老家。他在家一住月余,闭门不出,老苏便找他谈心,问他意欲何为。他说他不想走了,想在老家创业。老苏让他谈谈创业计划,他养猪啊种蘑菇啊云来雾去乱说了一通。
老苏听罢,对他说:给我滚回城里去!要想回来,先把供你念书的钱还给我!
苏让只好返回省城。走之前他得到老苏五千块钱的资助。他以此做本,批发了一堆盗版书籍,以三轮车载着游街摆摊,过起了与城管斗智斗勇的生活,月底计算收入,居然比上班和推销内裤要强。苏让遂坚心以此为业。有了点积蓄后,他在图书城盘了个门店,做起图书批零,从此告别游击时代,干起了坐地生意。
这之后,苏让又试图回老家参加村委会选举,但是尽管他“打扮成成功人士”,再加上他的“大学生身份”,最后仍敌不过大方送礼给村民的“开煤矿的土豪”而败北。
事业无成情感偏也受挫。大学毕业后潦倒度日的苏让,他的感情生活和他的事业一样挫折:大学谈的美丽动人的女朋友另择高枝,万般无奈之下选择了面目“惊”人的谢春丽,勉勉强强的心理之下,一直不愿意成婚,蹉跎到了三十来岁依然家业难成。这样的苏让不可谓不挫败。然而,这样的苏让难道不正是当代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的真实生存写照吗?不必援引社会学的统计和调查数据,大学生就业的惨淡,城市年轻就业一族的生存艰辛,实乃当代中国人所共知、人所共见的事实。像苏让一样,这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当初都怀着一颗热情的、奋斗的、“坚信只要努力一定就会成功”的心,但是事实却如此冰冷,以致于他们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冰冷。直到有一天,意外的事情发生。对苏让而言,这件“意外的事情”就是父亲被拘禁。因为要搭救父亲,苏让先是四处筹钱,后来又试图卖肾,最后绝望以致计划自杀。幸亏谢春丽出手援助,最后才化险为夷。不过小说毕竟是小说,它构造故事,虚构意外和新奇,但真实生活中的无奈却是实实在在的——买房、结婚、父母养老、看病……哪一件比“父亲入狱”这样的事情轻松?这样看来,苏让这个小说中的虚构人物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也许正是这样的一种被普遍感知到的、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的“无奈”,在近些年成为了文学比较关注的热点话题。
对于这个话题的书写,我们会想到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也会想到余华的《第七天》。这些小说中都有对于当代大学毕业生生存困境的描写。尤其是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它和《苏让的救赎》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所描写的都是当代大学毕业生的生存问题,而涂自强和苏让这两个大学毕业生又都是农村出身,都遭遇过情感上的受挫,都颇为努力上进却仍难脱悲苦。只不过,苏让最后救出了自己的父亲,也找到了自己的女友谢春丽,与年纪轻轻身患绝症去世的涂自强相比,其结局似乎要好很多。但这里折磨他们的困境是相同的,即他们都为生计所迫,属于余华《第七天》里所描写的那种大城市里为生存挤压着的“鼠族”。
无论《苏让的救赎》还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近年这一题材的小说,往往还会塑造另外一类年轻的都市“成功者”形象。《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家境优越、工作不愁的赵同学是为此类,在《苏让的救赎》中则是慷慨潇洒、派头十足的朱律师。这位朱律师受谢春丽之托帮助苏让打官司,短暂的接触中,苏让始则为其自信、潇洒所折服,并暗自自惭形秽,继而则被其粗俗、无礼所惊讶、刺激,而有所不齿。在这里,小说特意描写这样一个人物,以和苏让形成比照。苏让和朱律师比照,完全处于下风:朱律师西装革履、豪车代步、高雅音乐作伴,苏让灰头土脸、一身寒酸;面临事情(苏克修的案子),苏让束手无策,只能甘受摆布,朱律师一出马便立即化险为夷、扭转乾坤。在这里,小说并没有透露朱律师的年纪,但通过他的行为举止、言谈、与谢春丽的交往等可以推测,他与苏让、谢春丽等肯定是年纪相仿的同一代人,但是其生活质量和水平却有天壤之别。当然,他们之间更重要的区别在于他们的生活能力,尤其是在城市中所掌握的资源、占据的位置:苏让出身乡村,工作在底层,从事聊以糊口的各种营生,人脉贫瘠;而朱律师则条件优越,对社会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把握,熟悉规则,善于利用,游刃有余。在小说中,朱律师的家庭背景并没有被详细深入地介绍,但我们或许可以推断:他应该不会是和苏让一样的寒门子弟。他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赵同学应该更相似:有着优越的家庭背景,从而在各种社会资源、人脉的占有上有着先天的优势。
年纪相仿的两个年轻人,他们的处境、能力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李清源在这里显然是要表达一种社会性的批判。不过,这种社会批判还是次要的,更深在的批判是在文化和精神层面。朱律师这个外表光鲜亮丽的人物却有着一个并不光鲜亮丽的内心——他取笑谢春丽,鄙视苏让,言语粗俗、缺乏修养。对这样一个“成功人士”的塑造,显现了作者对当代精神文化的一种忧虑——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批外表光鲜、内在腐败的“当代英雄”?这种精神文化忧虑不仅仅在朱律师身上体现,在苏让身上其实也有体现,在物质生活层面与朱律师有着鲜明差距的苏让,在精神层面却也并不比前者高尚多少,他对待女朋友谢春丽粗暴无礼、参加老家村委会选举弄虚造假,这些都说明着苏让人格和精神的种种缺欠。
一般而言,为了表达一种批判,势必应该在两个人物之间“构造”一种显在的对比,而物质占有和精神(尤其道德)水平的反差是文学表达社会批判的惯用手段。但是在苏让和朱律师之间,他们显在的对比只存在于其物质生活水平和能力层面,在更深层的内在精神层面,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我们所常见的那种反差,在他们之间,精神层面更多的不是差异,而是相似。这里显现出了作者自身的一种困惑,这种困惑即他有所批判、有所质疑,却无所肯定、无所皈依。或者说,他痛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值得批判的现实,却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改变。这种无奈和方方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所传达的无奈相比似乎更为绝望,因为在方方的笔下,涂自强毕竟被赋予了一种积极、乐观、憨厚、质朴的品性,虽然有着如此品性的涂自强仍不免遭受致命的打击,但是他的那种品性本身毕竟还昭示着或许有的希望,而在李清源笔下,苏让身上负载的“希望”却是如此渺茫。

不过,李清源在表达批判的同时,也在试图传达着希望。这种希望,主要寄托在两个人物形象身上。首先是苏让的父亲苏克修。这个人物在小说中虽然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作者对他也缺乏太多直接描写,而是主要从苏让的视角加以呈现,但他却可以说是作品中刻画最成功、最饱满的一个人物形象。作者对他的塑造,主要通过两个事件:第一个是他“残酷”对待病妻,第二个是他犯案被拘。小说开头首先写了苏让回乡途中听到的一个关于父亲的传说,在这个传说中,母亲死后脱生成猪,父亲寻找到之后当场把它摔死,这是对苏克修残酷对待病妻的一个暗示。之后还有苏让对家庭生活的回忆,以及他的道听途说,这些都似乎印证着父亲对待母亲的“残酷”,直到后来父亲出狱直接面对苏让轻描淡写地澄清原委之后,苏让才知道自己错怪了父亲——他非但没有残酷地对待母亲,反而对她很“有感情”。第二个事件中,苏让也是首先误会了父亲,他听信了其他人对于事件的描述,认为是父亲拒绝将捡到的钱财交公,而被女友(在苏让母亲死后所结交)举报导致被拘,并因此而对父亲心生鄙视,但经过多方了解才知道,真相是父亲女友试图分赃被拒所以才举报,而父亲捡到钱财拒绝交公,以及结交这个女友(目的是贪图其丈夫车祸去世后的赔偿金),甚至平时还“偷人几颗菜,顺一瓶酱油什么的,就为了省几个钱”,都是以备儿子结婚买房之用。通过从苏让的角度“了解”到的这两个事情,我们看到,小说实际上是以欲扬先抑的手法勾画出了一个用心良苦、让人疼惜的农民父亲的形象。这个父亲外表强硬甚至专横,对待妻子貌似缺乏温柔和关心,但实际上他外粗内细、刚中有柔。而通过苏让的双眼,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底层乡村父亲的令人心疼:他身无长物,“除了些衣物和简单的生活用品,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就连衣服也大都旧了,而父亲以前可是热衷穿新衣裳的”;“苏让从没想过,父亲也有权利选择他想要的生活方式,有权力用他自己的思维和眼光去观照这个世界,寻求他想要的自由”……
在这里,这个乡村父亲对儿子的爱和自身的卑弱构成的反差首先仍然是传达出了一种批判,但是他对于妻子、儿子的情感仍然让人感到温暖。这种血缘亲情固然并不具有太大的文化启示意义,但是它却是一切拯救的起点。对于苏让这个儿子来说,他颓靡的情感和生活当然也需要拯救,而这个拯救的起点也应该是对于父亲的爱这样的人性温情的逐渐复苏。
另外一个暗含着“希望”的人物是谢春丽。这个貌丑惊人的女子有着一颗温暖的心,她固然貌丑,或许也富有心机(和苏让的结交很可能是她有意设计),但当苏让陷入危机时她却始终不计前嫌、不离不弃,并大施援手,这说明了她心地的忠厚良善。而且从她在其他危急和非危急关头的表现也能看出,她在城市生活的能力和经验方面也优于苏让(所以苏让在危机中总是渴望她的陪伴和帮助),这证明了她的坚强和机智。所以整体来看,这是一个充满阳光、朝气的青年人,她代表着自强、上进、乐观、聪明、灵活、不服从命运、勇于争取、努力向上,乃是鲜活生动、富有现代感的一个人物形象。
当然,整体来看,这篇小说对于“希望”的表达明显弱于批判——不管是苏克修,还是谢春丽,他们作为文学形象本身固然有着一定的活力,但是在体现社会生活的本相和本质方面,还是弱于苏让这个人物形象。这里牵扯到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当代社会生活的本相和本质究竟是什么?第二,作者在面对这样的社会生活本相的时候,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他的情绪和判断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并不难于回答,当代社会生活复杂丰富,而仅就这篇小说所描写的题材对象而言,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社会转型时期青年人的人生命运问题。这是一个复杂、沉重、让人焦虑的问题,八十年代路遥的《人生》已经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新世纪后的今天,这个问题却依然尖锐。所以对这样一个问题的书写,本身便带有着“先天”的沉重。而面对这样一个令人沉重的话题,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自然也是沉重的,小说结尾最能说明这一点——从表面看,苏让接来了父亲,迎回了女友,但这个“大团圆”的结局依然是可疑的,真实的生活会像小说这么如意吗?即便苏让暂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他依然还要攒钱、买房、养老、看病、处理夫妻关系,这些生活琐事,哪一件都忽略不得,哪一件都不轻松。在这些考验面前,苏让的幸福会持续多久呢?我不相信作者真的会相信自己作品的结尾就是苏让这样的年轻人未来美好生活的开始,毋宁说,这样的一个结尾只是表达了作者个人的一种愿望罢了。而这愿望的背后,是更为显在的迷惘、困惑和焦虑。
然而,写作者的内心困境并不意味着文学的困境,甚至它还是文学走向混沌、厚重和博大的开始。在《苏让的救赎》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相对立的景观:乡村和城市。而对这两种生活景观的书写,后者似乎更为作者所熟稔——苏克修的性格及其家庭、他“破败的农家老院”、让苏让“折戟沉沙”的村委会竞选……这些都包含着更丰富复杂的可供发掘的内容。而与之相对的是,作者对于城市生活的书写却是较为概念化的,围绕苏让的城市生活着笔不少,但多粗线条勾勒。而当“城市”和“乡村”两种景观直接面面相对时——比如朱律师随苏让回到苏家的老院子寻找办案证据——新晋的城市成功者朱律师和寒门子弟苏让的反应颇能反映作者本人的价值取向:“朱律师在他们的院子里溜达,东研究西观察,仿佛玩味古董,对这座破败的农家老院充满兴趣。苏让则在父亲的房间里翻箱倒柜。翻着翻着,苏让渐渐黯然神伤。”作者在这里显然是站在苏让、乡村的立场上的,这也是一种我们最常见的人文性的悲悯立场。但是这种立场对写作向混沌、厚重和博大的方向发展是否有益却是存疑的。
一种决绝的肯定或者否定,固然可以成就文学,而且文学经典本来也有多种风格和类型,然而对于小说这种本身带有“历史”性质的艺术体裁而言,特别是从社会转型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来看,混沌性、复杂性、丰富性才是当代小说应该努力追求的。李清源的小说能展现出这方面的素质,比如他对苏让这个人物形象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和塑造(既不刻意美化,也不刻意贬低)便能看出他对真实生活的尊重,但他似乎还可以做得更好——如谢春丽(甚至朱律师这个有些“扁平”的人物)能否写得更深入、立体一些?对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描写能否展开得更充分一些?这里都有更多可供深入挖掘的东西。
另外,从批判和拯救的角度来看,河南作家惯于批判,虽然他们的笔下也有“希望”和“寻找”,但整体来看,对悲惨、酷烈、令人绝望的生存环境、文化劣根和人性困境的表达似乎才是他们区别于其他地方作家的“标志”。这种几乎被推向极致的社会、文化和人性批判在刘震云、阎连科、李佩甫、墨白、邵丽、乔叶、南飞雁等笔下都能见到。他们这种对于中原的土地和人的书写,某种程度而言基本都是继承的鲁迅的那种批判性的文化启蒙传统,然而中原大地和中原文化是否有其他值得我们审视和发掘的传统?文学本身便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独立性的文化存在,它包含文化,但是也以其独有的方式创造文化,这种“创造”有赖于作者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感知、对历史的钻研、对文化和人性的思考、对自我的省察,等等。这是李清源这样的颇有才华的年轻作家需要继续努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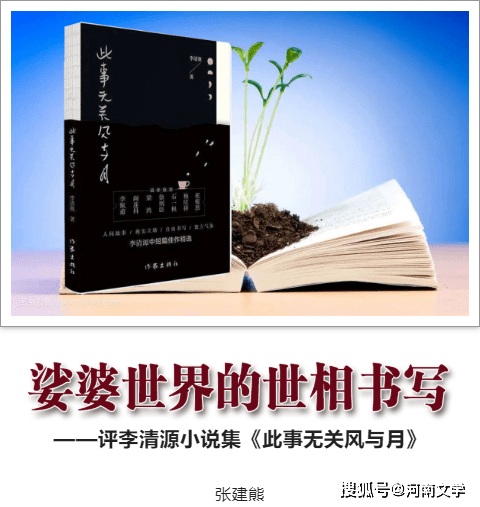
梁鸿说:“清源的文字,有某种神秘的睿智和老成,语锋机敏犀利,却又有洞透世事的宽容,对社会变迁和历史风云中的人性有极为准确的把握。”很难想象,这些话是用来形容一个青年作家的文笔及文风的,但确如梁鸿所说,李清源是当下少有的一个能将世相书写洞悉且明了如此的青年作家。此次,将他近几年发表的小说裒辑成《此事无关风与月》一书,其作品风格中的锋利之感与绵长之意更是展露无疑。《此事无关风与月》共收录了李清源包括《诗人之死》《一件口耳相传的往事》及《猎人与山贼》等十一篇中短篇小说,而这些小说之所以被选集在一起,是因为都有一个明显的主题表达——世相书写。毫无疑问,能将这些小说集合成一本书出版,这是对李清源关于世相书写的认同,是对他写作风格的褒扬,在这十一篇小说中,又可简单地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猎人与山贼》和《门房里的秘密》等为主的关于历史世相的书写,另一类则是以《诗人之死》和《无缘无故世上走》等关于当下社会镜像的模照。古语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无论是历史世相下隐喻的时代现实,还是社会镜像中反讽的当下妍媸,李清源的小说恰如镜、如史、如人,给自照者当头棒喝。
悬设、反转中的故事人生
《此事无关风与月》中的小说开头,往往自设悬念,且又自行解答,它提前告诉你谜题,又提前告诉你答案,看似给出结果,却又让你对故事发展的过程充满好奇。如首篇小说《诗人之死》,在第一段,它就告诉你死的诗人是谁,但除此之外,什么信息都没有,而由“诗人钟鸣之死”产生的“他因为什么而死?”“他是怎样的一个诗人”等疑问被留在了下文,让好奇者不得不继续阅读下去。在小说《猎人与山贼》中,李清源用“猎人凌晨入山,本欲捉一只山雉,却捉到一个山贼”。这三个单句组成一句话,简单明了地交代事情的起因和结果,但这句简单的话语背后却让我们产生了复杂的联想,“他是怎么捉到山贼的?”“捉到山贼后又会怎么处置?”……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联想一波随着一波。除了在小说开头巧置悬念,故事结尾的反转和与开头照应是其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在《无缘无故在世上走》中,其结尾处再三转折,一转是许诺靠着父亲的事故赔偿金买了一辆小车,就在夫妻二人对生活的前景充满希望的时候,两人乐极生悲,在路上撞死了人,生活重新陷入困顿;二转是许诺入狱妻子张燕都没有和他离婚,他觉得未来的生活还算有希望,却不想在出狱后见到妻子,妻子反而提出了离婚,其本来出狱后的振作姿态又被击碎;三转是妻子张燕得到了她们老家要拆迁的消息,她认为拆迁过后生活会有所改善,所以打电话告诉许诺不想离婚了,然而许诺已然选择了赴死。结局的一转再转,让故事的高潮一波接着一波,也让小说人物的命运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无缘无故世上走》的结尾那句“这家伙不会出事了吧?”又与开篇“第二次事故发生在三十四天后的中午”。隐隐间相连接、相呼应,让故事在第三次事故中戛然而止,让人意犹未尽的同时,又倍觉突然且发人深省。
法国著名剧作家贝克曾说:“悬念是兴趣不断向前冲、紧张和预知后事如何的迫切要求。”李清源在小说开篇就设置悬念,又在故事发展过程中采用插叙、倒叙与顺序并行的写作手法,利用限制视角将悬念悬置并延长,并通过结尾处的反转、多次反转及与开头的照应,将人物命运、故事走向和人性表达推向高潮的同时,又让整个小说的逻辑更加圆满,主题得到深化。其小说中这种极尽曲折而又充满意外的写法,可以说将时代之下,小人物命运随着时代浪潮的拨弄而起起伏伏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在大时代背景下,对人物命运的悲喜剧觉得愤然的同时又产生无能为力的惶恐,因为我们这之中的人,又何尝不是在时代的浪潮下起起伏伏,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是李清源笔下的某个人物或是下一个人物呢?
啼笑反讽中的三恶五趣
小说集《此事无关风与月》中的反讽多集中于故事人物的喜恶之中,借人物性格和行为中的“伪善”来揭露现实社会的“真丑”。在《此事无关风与月》这篇短篇小说中,李清源没有给小说主角取具体的名字,而是用“他”这个第三人称代词贯穿全篇,这其实是将“他”这个概念扩大化,“他”的形象又何止是一个简单的身份代称,何尝不是对世上千千万万个“他”的反讽,“他”者中的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阶段或是情景下都有着自己特定的身份,在这种身份的框定下,“他”有着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有着自己需要守住的底线,而在明知道出界行为的底线在哪,却依然触碰,并在底线外自我感动,又是何其可笑。另外一个“她”者的身份,又何尝是一个简单的形象化人物,“她”其实是诱使“他”或者说“他”者们突破底线的一个“魔鬼”,正是在“她”的诱惑之下,“他”者失去了自我,沉浸在自己本不应该沉浸的感动里无法自拔,“他”或“他”者看似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真谛,却丢失了“他”或“他”者最应该坚守的底线和道德。在小说《诗人之死》中,啼笑皆非的人物行为让反讽更具意义。潦倒诗人钟鸣的死亡,让文联主席杨宗初“粉墨登场”,借助杨宗初的视角,李清源通过插叙、倒叙等手法将“诗人之死”这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细枝末节娓娓道来,并结合杨宗初的身份,通过其对诗人钟鸣的蔑视、对作协主席吴学圃的嘲讽、对“女诗人”刘小柳的“栽培”等一系列行为,将当下诗人、作家的尴尬现状及乱相摹写得绘声绘色,也对当下社会看人下菜碟、身份比实力重要等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反讽是表现世情百态和社会现实的常用手法,在鲁迅的作品中,反讽更是其一大特色,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在评价鲁迅的作品时说:“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如果说鲁迅的作品是对当时那个至暗时代的嘲讽的话,那么李清源的作品就是对当下社会陋习和现实丑态的揭露,但这种揭露并不是一丝不挂地曝光在太阳底下,而是披着一层“伪善”的外衣,只有扒开它,才能让阳光显出内里的“真丑”。或许李清源难以达到鲁迅先生的高度,但我相信,深具讽刺意味且意蕴悠长的小说集《此事无关风与月》,将不会是个让读者轻易忘却或抛弃的作品。
诗化隐喻下的众生皆苦
诗化语言的运用在李清源的小说中非常普遍,而其小说诗化的表现可从遣词和造句中看出。首先是遣词,在此次集合成册的小说中,充分体现了其中原叙事遣词的精细,除了一般的俚语和方言,李清源在用词的选择上讲究准确而又诗化,且这一手法在书中比比皆是,如在表达嘲笑时用的词是“嘲诮”,在表达集合成册的时候用词是“裒辑成册”,在表达迎接时用的是“迎迓”,还有对不同的“看”的用法,如“猎人乜他一眼”、“寨主眄视猎人”、“张燕睖他”等,既是人物神态、表情的细节描写,又是隐喻的浅层表达。除了用词的考究、严谨和诗化之外,在小说中,其整个段落也呈现出明显的简练的诗化,如在小说《猎人与山贼》这一段:“寻到一条偏僻小径,忽闻有鼾齁之声隐约传来,似是有人在林中酣睡。此山是伏牛余峰,不甚高峻,亦无巨兽,但也时有野狼土豹出没,睡卧其间并不安全。何况时局不靖,内贼未熄,外寇又至,常人昼行尚且心生畏惧,此人有胆夜宿山林,若非剪径的强盗,就是夤夜赶路的壮士……”李清源的遣词造句凝练而简洁,顿挫而富有韵律,整个语句或是段落的叙事一气呵成,既有对后续人物的猜想,又有对“山贼”身份反转的隐喻。除了叙事的语句、段落诗化,在景物及环境描写上,李清源的诗化现象就更加的明显且凸出,如在小说《青盲》中,这段关于环境的描写:“午后果然下起了雨,不大,但很细密,淅淅沥沥的,淋湿了整个城市。天气骤然冷起来,街上行人稀疏,高高低低的楼房抑郁而立,在瑟瑟冬雨里缩成一团。我撑把雨伞,穿过老城狭窄的巷子,来到西关桥头。那棵老桐树依旧在落叶,一片接着一片,被雨水挟裹着,沉甸甸地坠到湿冷的地面。……”环境和景物的描写不同于叙事,用语虽少了些顿挫,但却多了份韵律,其特点也更偏向于现代散文和新诗,既有散文优美和谐的词句,又有新诗自由开放的形式,很值得借鉴和一读。
语言的诗化在结构上讲究的是句式灵活、整散结合,在内容上讲究的是形象生动、凝练含蓄,而在表达上讲究的是感情丰沛、内涵深刻。诗化是创作者文学功底厚重的外化,毫无疑问,李清源的小说很好地做到了这种诗化,且他优美的诗化表达,在对比中更衬出现实的丑陋,而也正是在他优美的诗化隐喻下,藏着的是底层人民的悲欢离合,是他对芸芸众生的浮沉痛悟。为官者不思大众,在蝇营狗苟中寻求迷途的快感;底层群众为着生存而活,在一时的得失中悲喜交加。所有人都在苦痛中浮沉,有人的苦痛显得讽刺,而有人的不堪却让人心疼;有人的得意让人不忿,而有人的失意却让人可悲。在李清源的诗化隐喻下,大时代背景中的小人物怎么都抽离不出“苦”这一主题,“乐”是苦中“乐”,“苦”是苦中“苦”,人永远在生活的苦痛中浮沉,在生命的苦痛中轮回。
阎连科说:“小说终归是世相之书,在尘情中昭示人性,混沌中窥见灵魂,于荣枯无常之境,发现时代的本相与生活的本真。”而在他看来“(李)清源的写作深谙其道”。小说是世相之书,而李清源的这本《此事无关风与月》正是对这当下娑婆世相的深刻揭露,在这一小说集中,李清源可以说是将世情洞察入微,将人物刻画入木,又以其犀利的笔刻、隐喻性的嘲讽及啼笑般的反转等手法,将情节构述得跌宕婉转,让小说阅读感极强的同时又不失文学性和艺术性。“此事无关风与月”化用自欧阳修的《玉楼春》,整句是“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只不过,李清源去掉了前一句,又将“恨”字变成了“事”,“不”变成了“无”,让其更适合小说“无关风月,却隐喻世事”的主题。《此事无关风与月》既是小说集的书名,又是小说集中最后一篇小说的题目,而这题目也更像是作者因为对世相讽刺太过深刻及大胆,而做出的无谓解释。
《此事无关风与月》是近两年颇受文坛关注的青年作家李清源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也是他的首部精选小说集,代表着他在中短篇小说创作领域的成就。
李清源的小说好看耐读,这不仅源于他较为丰富的生活积累,更在于他不动声色却有痛感的叙述功力。人生百态、现实镜面在绵密的生活流中无缝交融,各色人物在这交融中就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侧面的复合体,这种带着生活毛茸茸气息的各色人物,折射出生存场中现实的纹理,汁液饱满,真实灵动,具有不尽的言说性,这是作家的追求,也是文学的旨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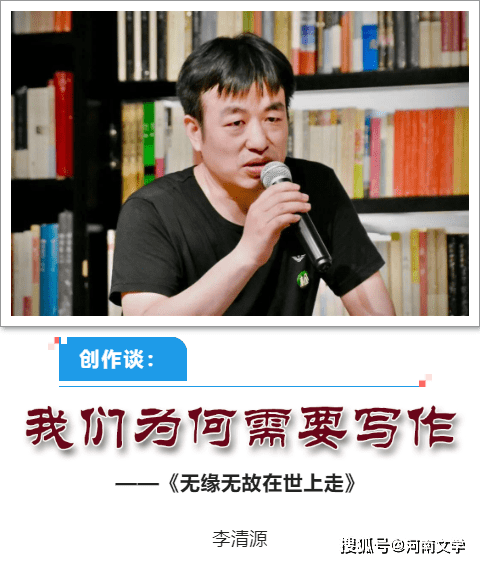
众所周知,现在文学非常边缘,社会大众关注文学的人很少,有限的大众关注,也常局限在几个话题人物身上。在这样的时境下,写作者要想通过文学换取一些现实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
作家要在作品里描写命运,个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乃至于全人类的命运,但作家本身,却很难通过作品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据说以前能,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能,但现在不能了,就算有,也因数量之少而不具普遍意义。妄图通过写作来求取名利,绝对不是一个好主意,在大街上卖煎饼果子,都比写作赚钱得多。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写?
很简单:我们需要表达。我们需要用文学这样一种形式,来表达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境遇,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得失成败和欢喜悲伤。所以我们要写作,不管有没有人关注,也不管是否会有回报。这就譬如喝酒,明明知道喝酒没什么好处,为什么还有人要喝?因为酒可以浇愁,可以忘我,可以在醺然中暂时放下所有的执念和痛苦,从而得到片刻的欢愉,一时的解脱,所以他们要喝,欲罢不能。
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同样,我们的写作,也不能因为无人关注而停止。是我们需要写作,不是写作需要我们,正如是兰草需要世界,而不是世界需要兰草。我们写得好了,固然可以为世界增色,但我们不写,也无损于世界的丰富与多彩。明白了这个关系,自然就会心平气和。
人生如此凉薄,我们需要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