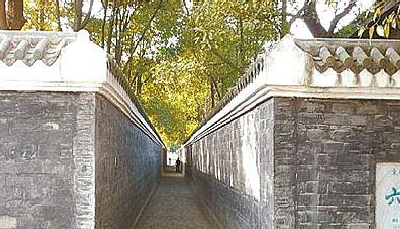
桐城清河张氏家族,世代以学术、诗文、艺术传家,不仅是一个累代甲科的簪缨世家和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而且是清代声势最为煊赫的政治世家、文化世家和名门望族。“自明隆庆二年(1568年)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之间的306年内,张氏10代人中先后有23人考中进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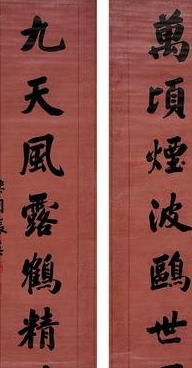

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乐圃、龙眠庄叟。康熙六年(1667)进士,选庶吉士,后迁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康熙十六年(1677),清廷颁诏,开始选拔一些作风朴实、做事果断、学问精深的人,每日侍从皇帝身边,以备顾问或征诏;同时设立南书房,张英被诏选入内,并赐其居住于西安门内瀛台之西,由此,开清代词臣赐居禁城之先河。
时康熙帝“益器重,以为可以大用”,凡“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必以英从。一时制诰,多出其手。”旋迁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历官兵部侍郎、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等。张英忠心事主,办事机敏,敬业勤勉,才思横溢,“每奏一章,上未尝不称善也。”康熙帝夸奖张英“老成敬慎,始终不渝,有古大臣风”。张英病逝后,康熙帝在祭文中赞誉其“公而忘私,真一心而一德;清而不矫,洵无倚面无偏”;雍正帝颂他“流芳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

张廷玉是清朝的重臣,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他一生谨慎,谨信“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信条,实心做事不事张扬。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很得圣宠。是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砚斋。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历任内阁学士、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职,深受康熙帝器重。雍正帝即位后,“(张)廷玉(因)周敏勤慎,尤为上(雍正帝)所倚”,历官礼部、户部尚书,文渊阁、文华殿、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等职;雍正八年(1730)清廷设军机处,任张廷玉为军机大臣,襄赞朝纲和军国机务;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帝病危,与鄂尔泰等被任命为顾命大臣。
乾隆帝登基后,命张廷玉与允禄等总理事务,因总理事务敬慎周详,特恩晋三等伯,赐号“勤宜”,清朝文臣爵至侯伯从张廷玉开始。为官期间,曾充乡试同考官、会试正考官和阅卷大臣,为朝廷选才甚众。乾隆十二年(1775),张廷玉病逝,赐祭葬,配享太庙,由此,开大臣配享太庙的先例,张廷玉是清代获得此殊荣的唯一汉族大臣。
张廷玉历事康雍乾三代,“清忠和厚始终不渝”,“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登朝垂五十年,长词林者二十年,主撰席者二十四年,朝廷大制多出公手,凡军国大事,奉旨商度。”[16]雍正帝谓其,“气度端凝,应对明晰,……居心赤忠,办事敬诚”,是堪任大事的“伟器”,为“我朝之贤大臣”,对张廷玉眷注尤深,荣冠臣僚,特御书“赞猷硕辅”四字,命内廷良工精制龙匾以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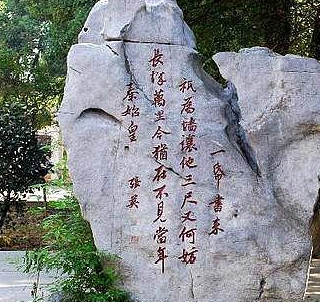
张英立朝近三十年,张廷玉居官五十余年,先后均身居要职,官至宰辅,成为朝廷的枢要之臣;父子二人才高识广,学问精深,长于文辞,著述丰富;真可谓政声文章,闻名遐迩。
在学术和文学诸方面造诣颇高,成就卓著。张英曾授命充《国史馆方略》、《一统志》、《政治典训》、《渊鉴类函》、《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著有《笃素堂诗文集》、《存诚堂诗集》、《周易衷论》、《聪训斋语》、《恒产琐言》等。
张廷玉曾以总纂官的身份领导主修《三朝实录》、《明史》、《雍正实录》、《康熙字典》、《玉牒》、《治河方略》、《大清会典》等重要典章史籍。著有《澄怀园文存》、《澄怀园诗选》、《澄怀园语》、《澄怀主人自订年谱》等书。

在唐朝初年,也有一门仨宰相的传奇,这就是南阳棘阳人岑文本,文本字景仁,自岑文本始,其从子岑长倩、孙岑羲相继为相,一门三相,令人惊叹。
贞观元年,授岑文本为秘书郎,兼直中书省。唐太宗行藉田(古时帝王春耕前农田,以奉祀宗庙)之礼,岑上《藉田颂》;元日(正月初一),太宗大宗群臣,岑又上《三元颂》,文辞均佳,很有才名。经李靖举荐,擢拜中书舍人。后又任中书侍郎,曾与令狐德芬撰修《北周书》,其中许多史论出于文本,最后官至中书令。
第二代为相的岑长倩早年父母双亡,由叔父岑文本抚养。曾任兵部侍郎,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岑长倩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与朝政。垂拱年间,自夏官尚书(即兵部尚书)迁为内史。垂拱四年(688年),李唐宗室起兵反武则天,岑长倩出任武则天后军大总管,征讨越王李贞,获胜。天授元年(690年),岑长倩拜为文昌右相,封邓国公,权势仅在武承嗣之下。天授二年(691年),加岑长倩特进、辅国大将军。
第三代为相的岑羲(?-713年),字伯华,中书令岑文本之孙。文昌右相岑长倩之侄。岑羲进士出身,历任太常博士、郴州司法参军、金坛令、汜水令、天官员外郎、中书舍人、秘书少监、吏部侍郎。
710年(景云元年),岑羲升任右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便被罢相,出任陕州刺史。712年(先天元年),岑羲再次拜相,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后以保护睿宗之功进拜侍中,封南阳郡公。
对照这两个显赫家庭,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可谓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在那个学得文武艺,售于帝王家的帝制时代,人生的通途就是科举取士,成就功名,因此这种人身的依附关系就先天地注定了伴君如伴虎的命运,张英父子一生唯谨慎,岑文本勤于政事,高官而忧,方得善始善终,但岑长倩和岑羲叔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个被诬陷谋反,下狱诛杀;一个依附太平公主,图谋不轨,最终伏诛。这也正是岑文本所担心的“非勋非旧,滥登宠荣,位高责重,古人所戒,所以忧耳。”,此为官之大防,至今仍有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