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荀子游历稷下学宫时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乐论》。在文章中,荀子从四个方面描述了乱世(或称末世)之征,后来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荀子真是目光如炬。当出现他文章所说的四种现象时,这个社会就将出现乱世征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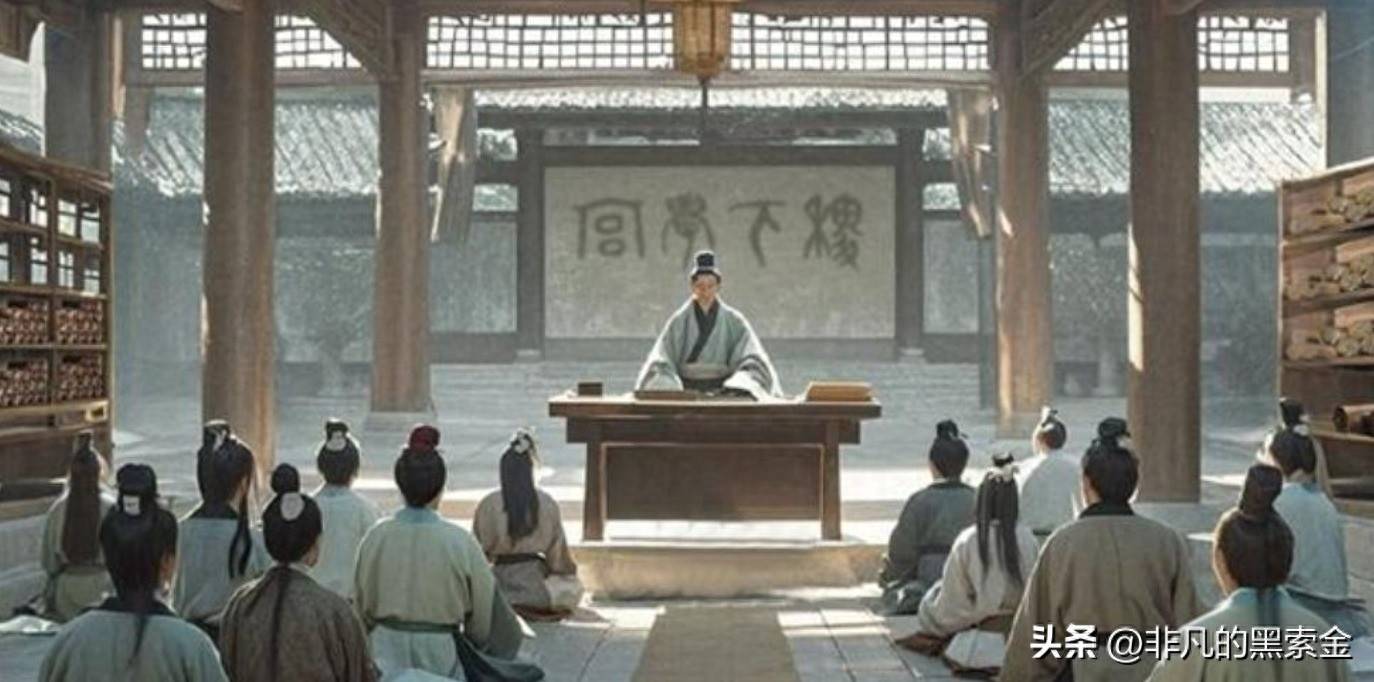
这四种典型现象就是“ 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奇装异服、性别失序、伦理堕落、利欲横行”,也即四维崩溃。今天看来,有些现象已有苗头,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警惕。
其服组,服,就是服装,组,就是过分雕饰、华丽繁复、奇装异服。在荀子生活的时代,服饰绝非简单的遮体之物,而是“别贵贱、明等差”的符号系统。男女穿什么服饰,能穿什么服饰,都有明确的规范。
而乱征之一的“服组”,就是对这种规范的瓦解:底层庶民僭用贵族的“玄纁”“朱绂”,游侠剑客身披“错彩镂金”的胡服,妇人头戴“步摇金翠”,突破“首饰不过三”的限制等等。 更有甚者,以“断发文身”“被发左衽”等蛮夷之俗为尚,故意模糊华夷、尊卑的界限。

这种服饰混乱的背后,是“礼”的权威性被消解。正如《管子·君臣下》所言:“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服饰失序,本质是社会成员对等级秩序的集体漠视,是秩序崩塌的直观信号。
其容妇,容,指仪表、姿态。妇, 这里并非指女性本身,而是指男子模仿女子的仪态举止(如柔媚、轻佻、妖冶),缺乏男子应有的刚健庄重之气。即性别角色的混淆和社会风气的萎靡、柔弱、缺乏阳刚正气。
在荀子生活的时代,男人以色事君的风气盛行,如龙阳君、安陵君,男人傅粉已经成为时尚,男人或柔媚扭捏作态,或轻佻浮浪举止失度。

荀子认为, 若男子失其刚健,便会滋生“畏葸苟且”之风:面对国难则“裹足不前”,面对不公则“噤若寒蝉”,面对责任则“推诿避责”。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流行“容妇”的六国很快被男人刚柔得体的秦国所灭。魏晋流行“容妇”而招致五胡乱华。南朝梁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晚唐的长安阔少“傅粉施朱、佩玉鸣鸾”为时尚,甚至模仿女子的“莲步”,讲究笑不露齿。
这种仪态的异化,表面是审美变迁,实则是精神气质的堕落。出现这种征兆后,无论是魏晋、南朝梁还是晚唐,都很快灭亡。可见其危害之大,不得不防。

其俗淫,是指两性关系的失序。俗,是指社会风气。淫,不是淫秽,而是过度、放纵,不合礼法。
荀子说,这具体表现为“三重失范”,即婚姻不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奔、纳妾成风;两性交往突破“授受不亲”的界限,甚至出现“桑中之约”“逾墙相从”;更有甚者,“烝报”、“倡优”(男宠)等现象公然挑战人伦底线。
这使得礼法廉耻观念荡然无存,人际关系混乱无序。在讲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年代,它让“家不齐、国不治”,不仅摧毁了家庭的稳定,更瓦解了人们的道德共识。
当贞洁和孝悌成为笑谈,当出轨和私通被视为风流之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便不复存在,社会秩序失去了最基础的伦理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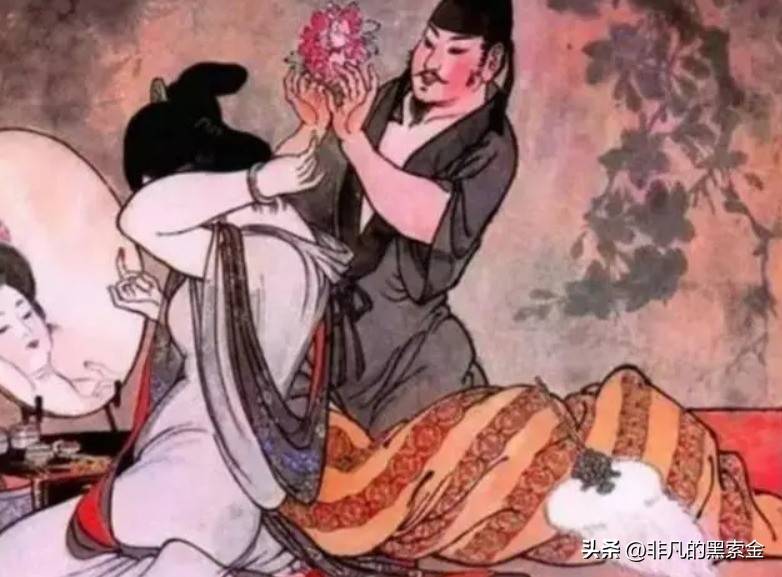
其志利。志,指志向和追求。利,指私利、物质利益。意为人们的追求只在于个人私利,唯利是图,缺乏道义、公心和社会责任感。社会失去了高尚的价值导向。
具体的表现就是商人囤积居奇、为富不仁,士人朝秦暮楚只为干禄求仕,官员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以充私囊,甚至普通百姓也“父子兄弟不相保,乡里朋友不相恤”,只因利字当头。
《史记·货殖列传》虽肯定“求利”的合理性,却批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的极端逐利之风;而到了乱世,这种风气更演变为笑贫不笑娼、灭绝人伦以求利的疯狂。

荀子说,当“利”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社会的合作基础便不复存在:商人不再愿童叟无欺,农夫不再愿勤耕为本,士人不再愿修身齐家,官员不再愿为民请命。
《乐论》中的“乱世之征”,以“服、容、俗、志”为镜,折射出的是整个“礼”的体系崩塌,而这个“礼”可视作今天的三观、秩序。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这四种征兆往往形成连锁反应。 服饰的混乱模糊了身份认同,性别气质的错位削弱了精神力量,淫佚之风腐蚀了道德根基,功利思想则彻底瓦解了价值体系。
荀子没能亲眼看到秦灭六国,但他肯定想不到,曾经刚键笃实的秦国,在平定六国之后也很快就陷入了乱世四征,似乎这是一个走不出的怪圈。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当我们重读《乐论》时,更应该引起极大的警惕,因为消费主义盛行、娱乐至死等现象,不过是“四征”的另一个名称而已。


